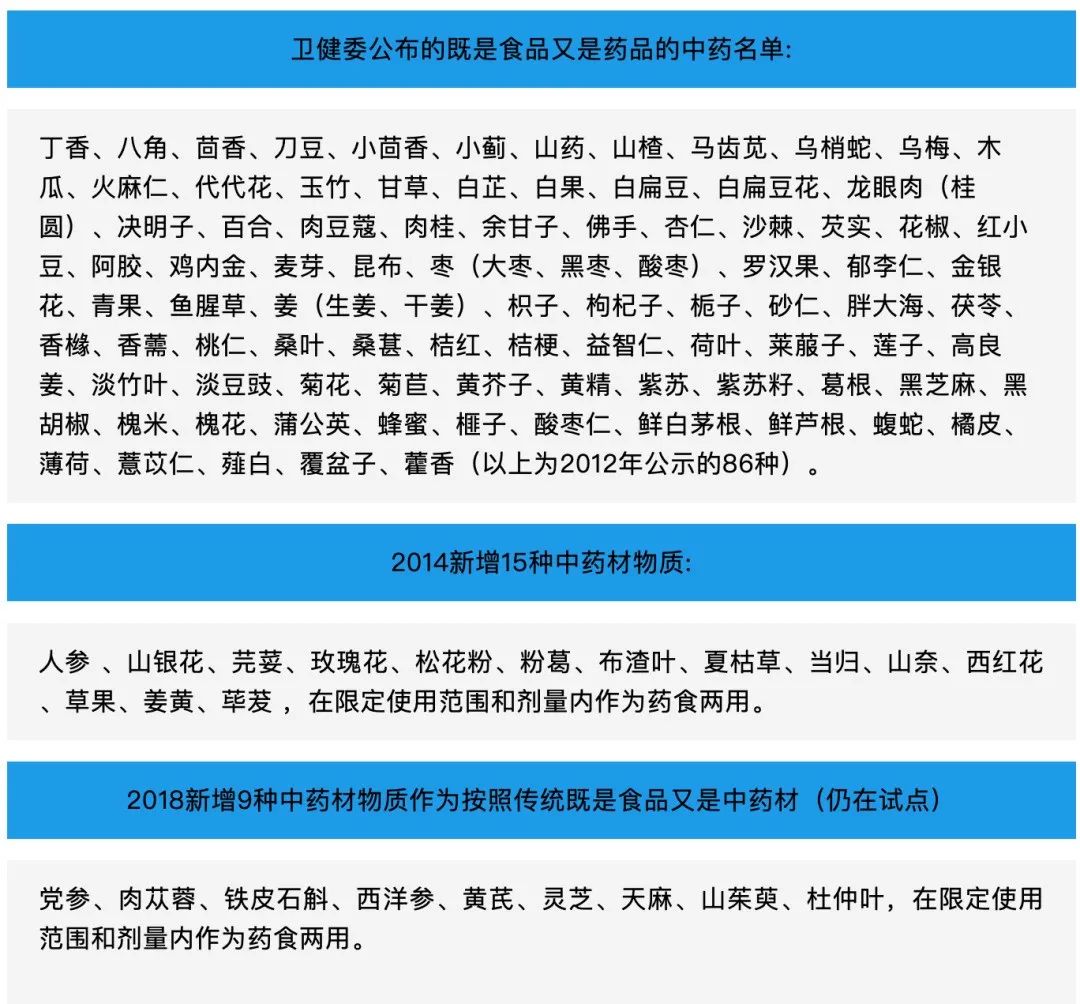【经典名方】经典名方药物考证关键问题分析与要点建议
时间:2023-04-24人气:作者: 药夫
经典名方药物考证关键问题分析与要点建议
詹志来 1 ,张华敏 2 ,黄璐琦 3通讯作者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北京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3.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100700)
2021年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了《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在“基本原则”项内明确要求“古代经典名方的处方组成、药材基原、药用部位、炮制规格、折算剂量、用法用量、功能主治等内容作为中药3.1类研发的依据,应与国家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一致。”在此之前,2020年10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联合发布了《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及《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首方剂)》,在“关键信息考证总则”中明确指出“关键信息考证是经典名方开发利用的关键性、源头性问题,‘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考证研究中需贯彻的首要原则,在‘遵古’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前临床和生产实际,注重缕清经典名方历代发展脉络,尊重历史演变规律,正本清源,传承不泥古,用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去认识经典名方中药物的基原、炮制、剂量、煎煮法、功效等关键共性问题,为经典名方的开发提供依据。”在“关键信息考证内容”中涉及药学部分的主要为明确基原及用药部位、炮制3个方面内容。此外,《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中“药材研究”项下提出“鼓励使用优质药材为原料进行中药3.1类的研究和生产”“药材的产地应在道地产区和/或主产区中选择”。可见,古代经典名方药物关键信息考证主要解决基原、药用部位、炮制及道地产区4个方面问题,这些关键信息考证的正确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取样研发、基准样品制备与制剂生产。因此经典名方药物考证非常关键,有必要进行总结,提出改进方向,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
目前,针对本草考证的具体思路与方法相关研究较少,谢宗万于1984年最早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总结;《本草学》亦对此做过总结。针对经典名方而言,有学者对药物基原、炮制、复方制剂等不同模块的考证方法进行过探讨,笔者针对药物关键信息考证的原则与细则亦曾做过探讨。针对经典名方中组成药物的具体考证,不少学者及笔者团队已开展了较多工作,目前已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中涉及的绝大部分药物进行了考证。通过对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以往工作存在一些不足,如经典名方所用药物的生产链涉及不同环节,如基原、产地、药用部位、采收、加工、炮制、安全性等,以往对药物古今文献的梳理及考证不够深入,详于基原而略于其他。又如,以往基原考证多数采用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或地方标准等所收载基原的相应学名进行表述,对古籍做考证并得出基原考证结论,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分类学的不断发展,不同时期文献中学名变化较大,《中国植物志》及历版《中国药典》也随之不断调整,这方面变迁以往未做系统梳理。此外,不少考证类文章还存在综合性本草著作格式体例不熟悉、文献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因此,笔者就当前经典名方药物考证相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要点建议,以期为高质量推动经典名方药物考证工作提供借鉴。
就药物“考证”术语而言,最早可见于张存惠晦明轩版《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书,由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麻革所做的《重修证类本草序》中提出“自古人俞穴针石之法不大传……书成,过余属为序引,余谓人之所甚重者生也,卫生之资,所甚急者药也,药之考订,使无以乙乱丙,误用妄投之失者,神农家书也。”可见考订药物的名实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药安全,为历代本草家最为要紧之事。同时张存惠在螭首龟座牌记上所作《重修本草之记》中也提出“又有《本经》、《别录》,先附分条之类,其数旧多差互,今亦考正”。此外,《证类本草》所存《嘉祐补注总叙》中亦提及“其开宝考据传记者,别曰‘今按’、‘今详’、‘又按’,皆以朱字别于其端”,后世对药物相关知识的整理亦多冠以“考订”“考正”“考据”“考证”。现代词语解释“考证”的含义多为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考据”与“考证”意义相同,而“考订”则为考据订正之意,即有通过考证加以订正。同样,“考正”意为考查订正。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均有对药物进行考证之意。然而,需注意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古代的名实考订与近代以来的考证并非完全一致,其内涵存在较大区别,由此可划分为我国古代药物考证和近代以来的本草考证2个不同阶段,其核心区别点在于是否采用了近代物种分类的思想与手段。
1.1古代药物考证
语言具有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文义出现变化,后人阅读前人的文献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间隔时间越久则阅读理解越困难。此外,对事物的认知水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诚如《四库全书总目》云:“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超远,传疑弥甚。”因此不同时代的学者便以当时的通俗语言或认知水平及思维方式对前朝文献作注解,即以今释古。对于以天然界物质入药为主的中药而言涉及大量自然博物方面的内容,在近代西方物种分类知识体系尚未引入我国之前,古代学者对药物考证主要为分为名物训诂与古代本草考证。
名物训诂是古代药物考证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部分内容散在于古代经史相关著作中,如在传统小学之中,训诂之学首推《尔雅》,该书中有多篇关于动植物的名物解释,如有关植物的《释草》《释木》,有关动物的《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其中,《释草》涉及“术,山蓟”“莔,贝母”“艾,冰台”“芐,地黄”等;又如《释木》中提及不同产地名称、不同品种及不同形态的枣:“枣:壶枣、边要枣;櫅,白枣;樲,酸枣;杨彻,齐枣;遵,羊枣;洗,大枣;煮,填枣;蹶泄,苦枣;皙,无实枣;还味,棯枣。”书中不少古代植物名称见于《诗经》《楚辞》《山海经》。然因其年代久远,释义也过于简单,因此汉代后有诸多学者对其作注作疏,其中较为知名的当属晋代郭璞,据邢昺《尔雅疏叙》载:“其为注者,则有犍为文学、刘、樊光、李。惟郭景纯用心几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郭璞凭借自己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多种动物或植物的形态、特征或生态进行了描写。郭璞的注解为后世了解《尔雅》中名字所对应的实物提供了很多信息,不少内容被历代本草学家所引用。类似的名物训诂或相关知识的著作尚有汉末刘熙撰写的《释名》、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三国吴陆玑所撰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清代徐鼎纂辑的《毛诗名物图说》等。另外,由于我国古代不同地区语言习惯、发音等均有所区别,因此同物异名现象较为常见,例如“饴糖”,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习称不同,分“饴”和“饧”。又如南方不同省内方言差异较大,同个省内各地区之间同个植物有不同的称呼,而有些称谓在各地指代不同,导致混乱,因此需要将语言学相关知识加以利用。汉代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其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涉及较多当时不同地区的名物称谓。可见古代名物训诂虽然不是纯粹为医药卫生服务,然而,由于中医药所采用的天然界物质多数取自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植物或矿物,存在重叠,因此名物训诂为药物考证提供了有力帮助。古代不少医家在对药物进行整理、考证时经常引用名物训诂方面的文献,如孙星衍、孙冯翼同辑《神农本草经》时大量引用《淮南子》《太平御览》《尔雅》《说文解字》等书籍内容,详加考证,引证详实。同样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释名等项下亦经常引用训诂材料。
古代本草学家在文字训诂基础上,更加侧重动植物形态、习性、产地、气味、功效等描述,并逐步通过绘制药图形式加以补充,发展成较为独立的古代本草考证学科,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尤其是其总结的不少药材性状一直沿用至今,如防风的“唯实而脂润,头节坚如蚯蚓头者为好”、甘草的“赤皮、断理,看之坚实者,是抱罕草,最佳”、石斛的“生石上,细实,桑灰汤沃之,色如金,形似蚱蜢髀者为佳”、羌活的“形细而多节,软润,气息极猛烈”、升麻的“今惟出益州,好者细削,皮青绿色,谓之鸡骨升麻”、白鲜皮的“气息正似羊膻”等已成为确保基原、控制品质的重要手段;唐代官方组织力量修订而成《新修本草》对前朝文献之误进行纠正,如“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考其同异,择其去取”,并在此基础上首创图文并茂形式:“铅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成五十四卷。庶以网罗今古,开涤耳目。”北宋政府则参考唐代做法修订本草,并编撰《本草图经》,绘制了大量药物图形,加以文字说明,准确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采收、加工、炮制、性味、功能主治及配伍禁忌等,保存了不同产地的不同药图,为后世考订药物提供了大量信息;其后各朝均有发展,如南宋《履巉岩本草》、明代《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本草原始》、清代《植物名实图考》等。我国历代本草按自然属性对药物进行分类成就最高的当属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然其是按照药物功能与形态相似度相结合进行归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方法,与近代以来的西方纯粹自然分类依然存在差异。
可见,受古代自然科学认知方法的局限,强调功用而弱于物种间细微差别的观察,也就是我国古代并无纯粹的自然分类体系,以致古代文献所述植物形态、生境及所画药图缺乏精细的分类特征描绘,进而导致同名异物现象突出,不同地域医家就地取材,有的是同属不同种,有的甚至是不同科的物种,其表述的精度用近代自然分类的标尺看则过于宽泛,存在指代不清的问题。因此,古代无论名物训诂还是药物考证均是在我国固有的自然知识认知体系下做的工作,与近代以来采用自然分类知识体系进行物种考订存在本质差异。
1.2近现代本草考证
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本草考证则是基于传入我国的近代西方物种分类学知识体系下的古代文献结合实物观察的工作,即用近代分类知识的标尺去丈量古代的用药范围。正如我国生药学家赵燏黄等在《现代本草生药学》第二章“生药学与旧本草学”第一节“生药学与西洋之本草学”中指出:“所谓本草学者,不限于植物之一类,探集动植矿等之材料,居自然科学(Historia naturalis)之地位,而利用于治疗方面者,此东西洋之趋向相同……惟东西洋所异者,西洋之本草学家, 多从所谓 Rhizotomi(探根家)之后,方产生希波克拉底氏(Hippcorates 460-377 B. C)之大医药家。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te 384-322 年殁)大哲人之门下,方造成齐物拉司之大植物学家(作植物史 Historia Plantarum 记 500 余种植物)。此等学者,早奠科学之基础,本草学时代转向植物学时代而过渡,故医药进行之途径,终有归纳。东方诞生神农而传《神农本草经》一书。虽历代贤君名哲,皆本是书相因相革,删补修订。然仅囿于本草之一门,终不达纯正科学之域。今试比较东西两方之本草,则知西洋之本草学与植物学之进步,占并驾齐驱之势。中国之本草学,单独发达而已,因初无植物学等相辅而行,故终陷于故步自封之境,诚堪浩叹……故本草学之权威,不因植物学之进步而稍减,且与植物学有相补发达,相得益彰之妙。卒能酿成近世的生药学(Pharmakognosie)(Materia medica)。由医药而分一种灿然大备之独立科学者,非数千年以来,受植物学家与本草学家之赐乎。”第二节“生药学与日本之本草学”中提及邻国日本:“于是日本之本草学与植物学,熔化而为一炉,结果则成植物学化的本草学,而本草学之进步,驳驳乎有直追欧美之势矣。嗣是以降,即明治维新以来。(即1868年以后)再由各种自然科学之掺入,煅炼镕铸而成之本草学,一变而为崭然独立之生药学矣”。第三节“生药学与中国历代本草沿革之关系”中则明确指出了本草考证:“古本草中之品物,经数千百年之历程,变迁亦极复杂。有存其名而实物不可得矣,有得其物而其名不相符矣。寻其绪而整理之,分其类而序列之,剖其物而实验之。得其成绩,预备加入现代本草的生药学,或为现代本草的生药学中,舶来生药之代用品。是则现代本草的生药,与古代本草的著录,关系綦切。故古代本草的著录,实研究现代本草的生药学唯一之参考书也。”蔡元培为该书作序时也指出,应以近代动植物分类学知识援古证今:“然而对于旧本草中所载诸药,为今日东西洋学者最注目者,莫如自然界生物之原料药也。而尚未能以近世动植物分类学的智识、解剖学的方法,参照实物,绘图写真,援古证今而确定之。故药品之是非真伪,聚讼纷纭,不能判别者犹是也;药名之复杂素乱,头绪分歧,无从稽核者犹是也。”赵燏黄在其所著另一部专著《中国新本草图志》凡例中提出“名称项下,用最近恩葛雷(A.Engler)自然分类法,并参考Botanicum Sinioum(Bretschneider),Chinese Names of Plants(Henery)及松村任三《植物名汇》、日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等书籍,考定本草之科名及学名而揭载之。其一时难于考定,并无实物或标本等参考者,则不敢武断,宁付阙如。考据项下,参酌古代本草诸家之说与今日科学上可以触类旁通、互相证明之处,而加以按语,其有欠合学理而涉于荒诞无稽,以及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诸谬说,则一律置之不论。”由此可见,近代以来的药物考证是以近代动植物学知识体系,尤其是物种分类学作为手段,对历代所存文献或实物进行整理的学科。
正如诚静容在《常用中药原植物的学名考正(一)人参、芍药、防风》的前言中指出:“在整理中药的工作中,原植物的鉴定与正名是一个最初步的基本工作。必须先确定了品种,认识了品种的特征,才能谈到中药的规格与检定。必须先认识正确的品种,获得正确的药材,才能够进行栽培、成分、药理及临床的实验及研究工作。中药的种类本来已经非常繁多,加以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植物种类又极丰富,所以一种中药常因地异物或因地异名。因此,在一个名称下常可取得不同植物所产的药材。同样地对于一种药材,其原植物的名称常不止一个,尤其在学名方面混淆情形更是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便在制定药材的标准规格上、选取实验研究材料上以及药物文献的使用上造成种种的困难。是以中药原植物的整理工作在今天是很迫切需要的。本文便是基于这种需要而进行的几种中药原植物的初步正名工作……正名的工作以学名的考据订正为主要环节,辅以正品植物的特征及与其相近种类的区别。”因而就考证的精度而言,传统与近现代有较大区别,加之物种分类学自身的不断发展,由经典分类发展到目前化学、分子等多学科综合证据支持的分类。因此,即便同样是近现代药物考证,也会随着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如Flora of China 对《中国植物志》不少物种做了归并等处理。《中国药典》不同版本亦不断吸收植物分类学界的成果而做出不同的调整。此外也应注意,由于植物分类学自身在不断发展,采用不同技术手段往往会得出不同的分类观点,互有争论,致使部分物种的分类学地位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而对于应用为主的中药而言,确保使用的物种不发生变化是首要的,至于以何种角度来命名或归属是其次,因此对于基原考证应尽量考虑以成熟而稳定的学名为界定,确保所用药物稳定、安全、有效。当现代学名所指物种信息与传统范围不符时需加以说明,如紫苏与白苏在植物分类上将二者作同一种处理,但历代入药选用的均为紫色叶型,因此在考订基原时应当明确入药选用品种为紫色叶型的Perilla frutescens。类似的尚有《中国植物志》目前将川楝 Melia toosendan 修订为楝 M. azedarach,与苦楝归并 为 1个种,然入药多为川楝 M. toosendan的果实。
受传统知识体系框架下的记录模式影响,加之古代绘图、印刷、影像等技术的局限,且不同文献作者的记录与绘画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在以近现代植物分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古代药物来源时需综合利用历代文献中有助于确定物种或其范围的信息,尤其是当古代文图描述缺乏分类特征时,历代提及的产地记载结合该属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分布则对于基原考证显得十分关键,例如李会娟等考证南五味子的基原时将古代著录的产地结合该属植物的野生自然分布情况,综合古代记载的植物特征加以细致的对比、排查,并取实物做形态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历代所用南五味子的基原为木兰科华中五味子 Schisandra sphenanthera。
此外,应重视除本草、医籍以外的其他资料利用,如我国历来有修志传统,现存万余种各类方志,内容丰富,包括全国地理总志(如方舆志、一统志等),各地方志(如省通志、府州志、县厅志等),各类专志(如山川志、边防志、都城志、宫殿志、苑囿志、祠墓志、寺观志、书院志等),各种杂志(如乡土志、物产志、风俗志、民族志、文献志、考古志、游历志等),以及外志(如环球志、一国志、多国志等),所记大至一国一省一州一府,小至一山一水一丘一墟,举凡历史沿革、地理形势、行政建置、物产资源等,靡不详尽,可从中汲取丰富的信息。其中保存了大量医药方面的史料,对于本草考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历代本草学家都十分重视吸收方志中有关中医药的史料,利用方志来搜集和考证药物的起源产地、品种、质量、栽培种植等。方志对医药工作者考证中药材品种,特别是当地特产中药和道地药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药材道地延续与变迁的第一手材料。方志在其物产类中大多数收录有当地药材情况,参看地方志,对于了解该地区药物资源分布情况、应用历史等大有裨益,说明方志在中医药发掘上有参考价值。方志、农书、花卉、笔记、小说等资料的综合利用可为不同历史时期药物基原与道地产区的考证提供支撑,目前这方面以往利用度不高,应当加强。
目前不少已发表的本草考证类文献因作者自身非专科专属的分类学者,且对于相关科属植物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分布情况、不同种之间的分类依据等缺乏基础认识,致使较多考证类文献仅着眼于古籍中较为明确记载的形态描述与药图,未能系统地对所有可利用的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利用,部分考订结论值得商榷。因此,建议从事本草考证的学者与从事专科专属的动植物分类学者共同合作,推进本草考证的纵深发展。
近代以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我国传统药物的考证多侧重基原的整理,如早期日本学者伊藤圭介、松村任三、大沼宏平、白井光太郎、牧野富太郎、石户谷勉、中尾万三、木村康一、岗西为人等,西方学者如师惟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英国)、奥古斯汀·亨利(Augustine Henry,爱尔兰)、贝勒(Bretschneider,Emile Vasil' ievitch,俄国 )、师图尔(Stuart,George Arthur,美国)、伊博恩(Read,Bernard Emms,英国)等。这些不同国家的学者多数是以《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本草图谱》《草木图说》等中日书籍的图文并结合实物样品采集进行考订。这些早期东西方学者多数为植物学服务,也就是说为了将东方的植物名与近代分类学名之间进行衔接,需要将中文所指植物相应的学名做出考证,而我国动植物记载从实用角度出发,在本草资料中最为丰富,因此在考证时多以本草类书籍作为研究资料,而这些早期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续我国学者自行开展药物考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国学者采用近代分类学方法进行药物考证的先驱当属赵燏黄,其后黄胜白、裴鉴、周太炎、吴征镒、诚静容、楼之岑、谢宗万、徐国钧、肖培根等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谢宗万对常用中药材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本草考证,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多数常用中药材的历代主流基原已基本明晰,相关考证成果已通过论文、专著等发表或出版,并通过《中国药典》得以应用,对我国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可控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考证主要以解决品种问题为出发点,原因是以野生为主要来源的时代背景下,受各地同名异物、近缘物种形态相似、药农野生采集难以准确区分等因素影响,当时面临品种问题突出,因此以《证类本草》《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为主要参考资料,把握历代主流,结合近现代实际情况,确定基原,以保证用药安全有效。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药物基原流变情况则多数未作全面分析,此外,对于经典名方所含药物的炮制、药用部位、道地产区等方面的考证亦涉及较少,仅部分炮制历史较为复杂的品种有专门文献做梳理,但均未站在经典名方开发角度,按照时间次序进行流变与断层考证。而对于经典名方所含药物而言,《目录》收录的100首方剂涉及朝代从汉代至清代,跨越漫长历史,需要根据方剂所处年代的用药情况加以选择,优先选择最符合原方时代特征的药物。此外,随着当前中药材生产模式的巨大变革,常用药材已基本实现人工生产,虽然基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但随之而来生产过程干预对品质影响较大,加之受经济利益驱使而无序引种、重量轻质等问题日益突出,对经典名方制剂高质量的开发、生产影响较大,需要通过古籍考证,挖掘古代药物生产、炮制及品质控制精华,为经典名方药物取样提供依据,引导高品质经典名方制剂生产。综上分析,经典名方的药物考证具有自身特点,突出历史变迁的脉络梳理,注重横断面分析,如不同时期药材的道地产区是随着基原与资源量而发生变迁、药用部位与炮制在历代应用中亦存在变迁。基于此,笔者团队按照经典名方药物考证的特点,对《目录》中的不少药物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考证,但相关工作依然值得不断深入。
本草考证的核心内容是药物基原的考证,而近代植物分类学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瑞典科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所著的《植物种志》于1753年出版,该书与1758年第10版《自然系统》首次将阶元系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这2部经典著作,标志着近代分类学的诞生。新的植物命名法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植物分类系统,使得追踪某种草药的原植物进而确定草药种类成为可能,因此被认为是革命性的。林奈命名法最大的价值在于其能够接纳并命名所有新的事物,兼具开放性和普遍性。此后建立的早期近代欧洲博物学致力于将外来植物一一纳入到现代植物分类法之中去。
对于植物来源性中药进行基原考订,并以林奈所创的双命名法对我国常见药用植物进行命名较早的当属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卢雷罗(Juan de Loureiro),其对中国澳门及越南北部等地的植物进行调查 ,并于 1793 年出版了《交趾植物志》(Flora Cochinchinensis),该书中对东南亚地区常见药用植物用林奈法进行命名,并注有植物的粤语拼音。虽然早于卢雷罗的尚有诸多学者,如西方植物学家到中国专业采集植物的第1人詹姆斯·昆宁汉姆(James Cunningham)及林奈的学生佩尔·奥斯贝克 (Pehr Osbeck)等,但均非专门针对药用植物。同时期,欧洲植物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到日本去考察植物,最早开始用林奈创立的双命名法为他在日本看到和采集到的植物命名,其于1784年出版了日本第1本植物志,其中涉及大量中药原植物,该书由日本植物学家伊藤圭介翻译考订而成《泰西本草名疏》,并于1829年出版,该书中伊藤圭介将通贝里所著《日本植物志》中植物学名按照首字母次序重新排列,以便于检索,同时在相应的学名下标注了植物和名及中文名,该书可视为最早考订中药学名的著作。然而其中不少学名系通贝里根据日本所见植物而定,植物中文名称多摘自《本草纲目》等著作,并参考我国多种本草、植物类书籍的附图,导致出现1个中文名可作为多个近似植物的通用名、多个学名所指植物都用1个中文名表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早期日本著作中较为常见,这就导致我国早期相关资料直接转引日本文献考订的结论,进而存在中文名对应学名所指植物并不符合我国实际,甚至存在不少根据日本所见植物而定的基原在我国并无分布的情况。如1917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序中提及“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概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取日本专家考订之汉名而用之。”赵燏黄在1933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生药学教材《现代本草生药学》中便已指出“原植物科名及学名,用最近恩葛雷氏(A.Engler)自然分类法及下山·柴田·药用植物学……等书籍,考定生药原植物之科名及学名而揭载之。力矫用和(日本)药之原植物学名,充用于国药之谬误。”
日本考订中药学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其在明治维新之前全盘采用中医药体系,且早期用汉语撰写科技类书籍,因此不少植物名称均采用汉语书写,加之受《本草纲目》影响巨大,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日本近代博物学。因此其考订学名对我国影响深远,然早期大多数日本学者均未能亲自赴我国做实物采集,因此不少植物仅是与本草所附图片相似而误订成我国中药的基原。与其相对的是早期不少西方来华学者在我国根据实际采集的植物或生药标本进行的考订,如俄国学者塔塔林诺夫(Alexander Tatarinov)、英国学者丹尼尔·汉璧礼(Daniel Hanbury)及师惟善、奥古斯汀·亨利、贝勒、师图尔、伊博恩等。然而受到语言所限,西方学者对于阅读和利用我国本草、农书等著作不及日本学者精通,未能对历代本草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多数根据药图形态加以推测,加之也未能对我国药物做全面的实地调查,因此部分考订的基原仅根据局部地区采集的实物而定,存在不符我国实际的情况,如早期文献将我国药用黄芪的基原定为贺兰山黄芪 Astragalus hoantchy 或秦岭黄芪 A. henryi,经过我国学者系统的调查、取样、鉴定后认为其不符合我国实际。我国近代以来最早开展基原鉴定的当属赵燏黄先生,如其在《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中对日本学者考订的玄参基原做了纠正:“玄参市品,当以杭州笕桥培植者最为著名,盖畅销全国之药材也。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如 Giles、Stuart、松村、中尾、木村、石户谷诸氏,均认为玄参科之Scrophularia oldhami Oliv.。查此种玄参,虽多生于我国北部,然北方药肆并未采用,惟朝鲜及日本用之;北方药肆之玄参,皆谓来自杭州,著者特移植杭州笕桥之玄参苗,即笕桥人之所谓乌玄参者,培植结果,知为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此种原型最初在宁波发现之,现今南北药肆所备之玄参,多为此种植物之干燥根部也”。可见,在整理近代资料尤其涉及不同时期学者考订的学名结论时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了解当时所采集标本的情况,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得出客观的评述结论。近代学名考订历史沿革的整理对于深入开展本草考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阅读和利用近代不同时期文献中所定学名时,若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与变化过程,则易误解,如我国早期不少植物学、药学著作转引的不同时期文献的学名,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对于近代学名考订沿革梳理以往工作较少,且未能全面系统的梳理,笔者团队在本期古代经典名方药物考证专刊中首次对近代部分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经典名方药物考证强调历史流变的梳理,在厘清古今变迁基础上尽可能尊重处方所处时期特点给出最合理的建议,即尊重原方原意。然而在历史发展中亦要看到,有些药物的基原、炮制、道地产区的变迁是临床优选的过程,同时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变化,且这样的变迁历经漫长历史检验。此外,亦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充分吸收当前各项研究成果,古为今用。考证梳理不是为了退回到古代,而是更好地为今人服务。例如,对经典名方中所用半夏、附子等毒麻类药材的炮制方法进行考证时,应通过梳理其炮制方法的历史演变脉络,并结合生产变革及现代研究成果,给出合理的建议。
例如,半夏的不良反应古代早已被发现并采取了相应的减毒措施,早期主要采用热水处理,如《武威汉代医简》记载:“半夏毋㕮咀,洎水斗六升,炊令六沸。”“毋㕮咀”即完整个子药材不经过切制等处理,意在对半夏表面的黏液进行去除。汉代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中提到:“凡半夏不㕮咀,以汤洗数十度,令水清滑尽,洗不熟有毒也。”该方法与《武威汉代医简》十分相似,也是用不经破碎的完整药材,将用水略煮改成热水即“汤”洗,要求“水清滑尽”,而且强调“洗不熟有毒”。其所谓“滑”的物质,即现代研究认为的半夏表面的黏液物质。从组织构造上看,半夏块茎的外层有多列木栓细胞。部分木栓细胞中含有黏液物质,草酸钙针晶成束含于黏液细胞中,且针晶束的结构较为特殊,如具有特殊的针尖状末端、针晶表面有凹槽和倒刺、附带某些毒蛋白(如凝集素),使得其不经处理时易引发咽喉等部位的炎性刺激。因此通过反复的热水处理,充分去除其表面的针晶束,可避免不良反应。张仲景使用半夏时多以“洗”注明其炮制要求。相近历史时期的《名医别录》中最早将“生令人吐,熟令人下。用之,汤洗令滑尽”的处理要求纳入本草。“生令人吐”恐即其对咽喉部所产生的强烈刺激,而“熟令人下”则说明经过热处理使其熟后则可下咽,具体使其“熟”的操作便是“汤洗令滑尽”,与张仲景所述方法完全一致。可见早期热水处理是半夏的主要处理方法。至于汤洗的次数,不同的本草或方书要求也不同,有5遍、7遍、10遍,或言净洗、汤泡、汤浸洗等,但目的相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仲景往往以生姜配伍半夏使用,且大多比例相当。《药对》中有半夏畏生姜的记载:“射干为之使,恶皂荚,畏雄黄、生姜、干姜、秦皮、龟甲,反乌头。”“相畏”出自《神农本草经》,后世总结认为其是药物之间的相互抑制作用,即药物毒性或不良反应能被另一种药物消减之意。可见生姜能降低半夏的不良反应,也是张仲景将二者配伍使用的原因,后世凡用半夏的处方往往加姜亦是源于此。正是基于此实践,逐步衍生出姜直接作为辅料来对半夏进行炮制的方法,如晋代《刘涓子鬼遗方》记载:“半夏(三两,汤洗七遍,生姜浸一宿熬过)”,这或是最早关于姜制的记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序录及正文中分别记载:“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方中有半夏,必须生姜者,亦以制其毒故也。”唐代《药性论》载:“汤淋十遍去涎方尽,其毒以生姜等分制而用之。”此后生姜制半夏成为历代医家公认的炮制方法,如宋代《宝庆本草折衷》言:“半夏以生姜制其毒,乃法之常。”元代《汤液本草》谓:“生,令人吐;熟,令人下。用之汤洗去滑令尽。用生姜等分制用,能消痰涎,开胃健脾。”可见半夏在热水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姜制,并成为历代医家所认可的最主流的炮制方法,姜制是可考最早的半夏加辅料炮制方法。针对生姜配伍半夏的功效机制,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生姜中的姜辣素类成分能抑制环氧化酶-(2COX-2)、前列腺素E2(2PGE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一氧化氮(NO)、丙二醛(MDA)的生成,减轻半夏毒针晶所致的炎症反应,从而减轻半夏的刺激性。同时,生姜能够增强半夏温化痰饮、降逆止呕的功效,明清时期医家对其协同功效多有探讨,如明清时期《药性粗评》《得配本草》《本草求真》中均记载半夏加入生姜共制可治用于治疗寒痰。从历史演变脉络来看,半夏与生姜配伍以减毒增效早有基础。
随着临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自姜制半夏发展以来,历代医家通过各种配伍以拓宽半夏的临床适应证,以满足不同病证的需求,故半夏的炮制由早期单一的汤洗逐步扩展到运用多种辅料与半夏共制。如逐步扩展了具有祛风、燥湿、清热等功效的白矾、皂荚、石灰、竹沥等辅料,发展出针对不同病证的半夏炮制品。白矾是生姜以外较早应用于半夏炮制的辅料。白矾最早可见于北宋时期,《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新法半夏汤”中记载了姜矾同制半夏的炮制方法:“大半夏四两(汤浸洗七次,每个切作二片,用白矾末一两,沸汤浸一昼夜,漉出,别用汤洗去矾,俟干,一片切作两片,再用生姜自然汁于银盂中浸一昼夜,却于汤中炖,令姜汁干尽,以慢火焙燥,为细末,再用生姜自然汁搜成饼子,日干或焙干,炙黄勿令色焦)。”又“牛黄生犀丸”一方中记载“半夏(白矾制)”。北宋另一方书《圣济总录》中则提到2种加入白矾做辅料炮制半夏的方法,即“白矾水浸七日焙干”与“白矾水煮焙”。南宋《宝庆本草折衷》对白矾制半夏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又与白矾相宜。然又有净洗薄切,瓷器贮之。每壹两,以白矾末叁钱,重铺其上,沸汤淋注,与药平满,浸一昼夜,嚼之不戟喉舌,曝为元散。”此法与当代“清半夏”制法已十分接近。其后明清时期诸本草方书均有加入白矾、甘草共制的记载,如《本草约言》曰:“常用亦以姜、矾、甘草煮之”,并已发现半夏与姜矾同制可用以治疗湿痰、清水痰。现代研究表明,白矾溶液中的铝离子络合毒针晶中的草酸钙,可使其分解破坏,又白矾溶液呈酸性,可以溶解或水解毒针晶中的蛋白,此双重作用使半夏的毒性显著降低。自明代起,半夏炮制辅料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加石灰水制湿痰、加皂荚制风痰、加甘草制寒痰、加竹沥制火痰等,据统计,历代半夏不同炮制方法记载多达30多种。
综上所述,半夏早期采用热水处理以减毒,同时以生姜配伍相畏使用;魏晋时期以来逐步发展成姜制;宋代开始逐步加入白矾、石灰等辅料,并运用发酵方法做成曲;明代进一步拓展到皂荚、竹沥等。但加入姜、白矾和石灰3种辅料的炮制方法为历代主流并延续至今,最终出现了生半夏、清半夏、姜半夏、法半夏4种炮制规格。传统半夏采取汤洗的目的为去滑减毒,然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则较难控制工艺,如水温受投料量的影响较大,且半夏原药材大小不一,小规模热汤洗较易,而工业化生产则难以控制均一。因此自宋代以来改进并新发展起来的白矾制清半夏延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并被历版《中国药典》收载,形成稳定可控的炮制加工工艺,其安全有效得以保证,鉴于此,建议经典名方汤洗半夏采用与古代炮制工艺最为接近的清半夏规格。
近年来发表了不少本草考证类论文,其中存在不少因文献学知识匮乏所致的不足,如不少论文引述古代本草相关记载时经常直接引用《证类本草》或《本草纲目》转引的其他书籍的内容,致使存在很多引文错误。如《证类本草》以《本经》为核心,自汉以降,代有增益,层层包裹,蔚为大观,宋代以前的诸多本草文献皆不传于世,主要依据《证类本草》之转引,其征引文献多达200余种,且其对征引的历代主要文献一律注明出处,使得《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嘉佑本草》《本草图经》等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得以基本保存。当然,唐慎微在引用时也存在原文照录、化裁引用、撮述大意、讹误引用、综合引用等多种方法,因此在引用《证类本草》时应熟悉其格式体例,避免直接标注为《证类本草》,对于转引的文献中有存世的,应尽量从一手文献中引用。亦可选用辑复的成果。同样,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通过原文照录、撮述大意、增字引录、减字引录、改字引录等方式大量引用了《证类本草》的内容,在这些引文中,除部分原文照录外,李时珍对大部分引文内容做了改动,这些改动有得有失。因此,在引用《本草纲目》的内容时应熟悉该书体例,尽量只引用李时珍自己所新增的内容,对于其转引的资料应核查原始出处,亦可通过李时珍转引的方法及其内容研究其处理的动机。近代文献资料中亦需注意,如1892年贝勒所著《中国植物》第三卷中,对《本草纲目》所载多数植物药做了整理研究,除对我国本草按年代成书次序加以原文翻译以外,还汇总了在其之前不同学者的观点,均逐一注明出处,类似的尚有1915年松村任三所著的《改订植物名汇·前编·汉名之部》,以及伊博恩于1936年出版的《本草新注》(第3版)等。在引用时,均应分清哪些是撰写作者本人的内容,哪些是转引他人的观点,避免将其转引的内容当成撰写者本人的观点。
历代本草关于动植物形态描述最为详尽的当属《本草图经》,因其为宋代官方政府组织全国力量收集实物样本,经专业画工整理绘制而成。此外,李时珍通过自身实践,对其所著《本草纲目》一书中大多数药物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其细致的观察,生动的记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重要的参考。因此,这2个资料成为后续诸多本草关于药物形态描述的来源,不少本草甚至直接加以合并精简裁化而来,如《本草原始》中的形态描述等基本通过《本草纲目》集解项内内容整理而成。因此在引用诸多本草内容时应注意原始出处,避免毫无意义的重复引用。此外,应注意资料的不同版本问题,不少已发表的考证类文章在转引古籍图片时存在错误,比如在引用《证类本草》所存《本草图经》的药图时直接标注为《证类本草》,这是不妥的,应该注明确切的版本。目前较为通行的是晦明轩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所存的药图,而《大观本草》(刘甲本)亦较为常见,亦有《绍兴本草》的手绘图,3个不同版本之间差异不大,因此一般引用晦明轩本所存药图即可。另外像《本草纲目》不同版本的图亦需注明,又如《本草蒙筌》的药图并非初刻原有,而是万卷楼版由刻书商补入,再如《本草原始》不同版本的生药图亦有区别。因此应尽量选择较好的版本并注明。
综上所述,经典名方药物考证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当前经典名方开发,为该类药品研发实践提供源头性依据。因此,需要对本草考证的现状、问题、成果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吸收前人的优点,补充以往考证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典名方药物考证自身特点,形成特有的研究体系。即注重历史变迁的脉络梳理,注重横断面分析,在全面分析基原、道地产区、药用部位与炮制方法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用药资源、习惯、风格的变迁基础上,充分吸收近现代研究成果,并结合当前生产力和认知水平,给出不同时期经典名方药物的合理关键信息,为经典名方的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2,28(10)
标签:
【免责声明】
1.“高鹏说药材”致力于提供中药行业各类资讯信息,但不保证信息的合理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不对因信息的不合理、不准确或遗漏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2.“高鹏说药材”部分文章信息来源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对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平台联系。
3.“高鹏说药材”所有信息仅供参考,不做任何商业交易及或医疗服务的根据,如自行使用“高鹏说药材”内容发生偏差,我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责任,赔偿责任。
4.“高鹏说药材”各类带“原创”标识的资讯,享有著作权及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网站协议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个人不得转载、链接或其他方式进行发布;经本网协议授权的转载或引用,必须注明“来源:高鹏说药材(www.gpsyc.com)”。违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本声明未涉及的问题参见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当本声明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最新文章

百花农品:真药材,平价卖,守护千年药香
在中药材电商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乱象丛生:染色虫草、硫磺枸杞...(1080 )人阅读时间:2025-02-27
破茧重生:民间中医的千年传承亟需政策松绑!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数千年来以“简、便、验、廉”的特点...(926 )人阅读时间:2025-02-25
理性看待民间中医的作用:传承与困境中的“高手在民间”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其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现代医疗体系内,更...(894 )人阅读时间:2025-02-24
让真药材回归百姓家——守护中药生态,百花农品与您同行!
中药,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健康密码,承载着“治未病”的智慧与自...(1025 )人阅读时间:2025-02-21


 目前中医药产业仍是以中药农业(中药材种植生产)为基础、中药工...
目前中医药产业仍是以中药农业(中药材种植生产)为基础、中药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 电商背景下现代中药材物流问题及对策研究赵翰林 李思屹 张藐丹...
电商背景下现代中药材物流问题及对策研究赵翰林 李思屹 张藐丹... 甘肃省道地药材枸杞子资源现状及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崔治家 邵晶...
甘肃省道地药材枸杞子资源现状及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崔治家 邵晶...